E滁网友,好久不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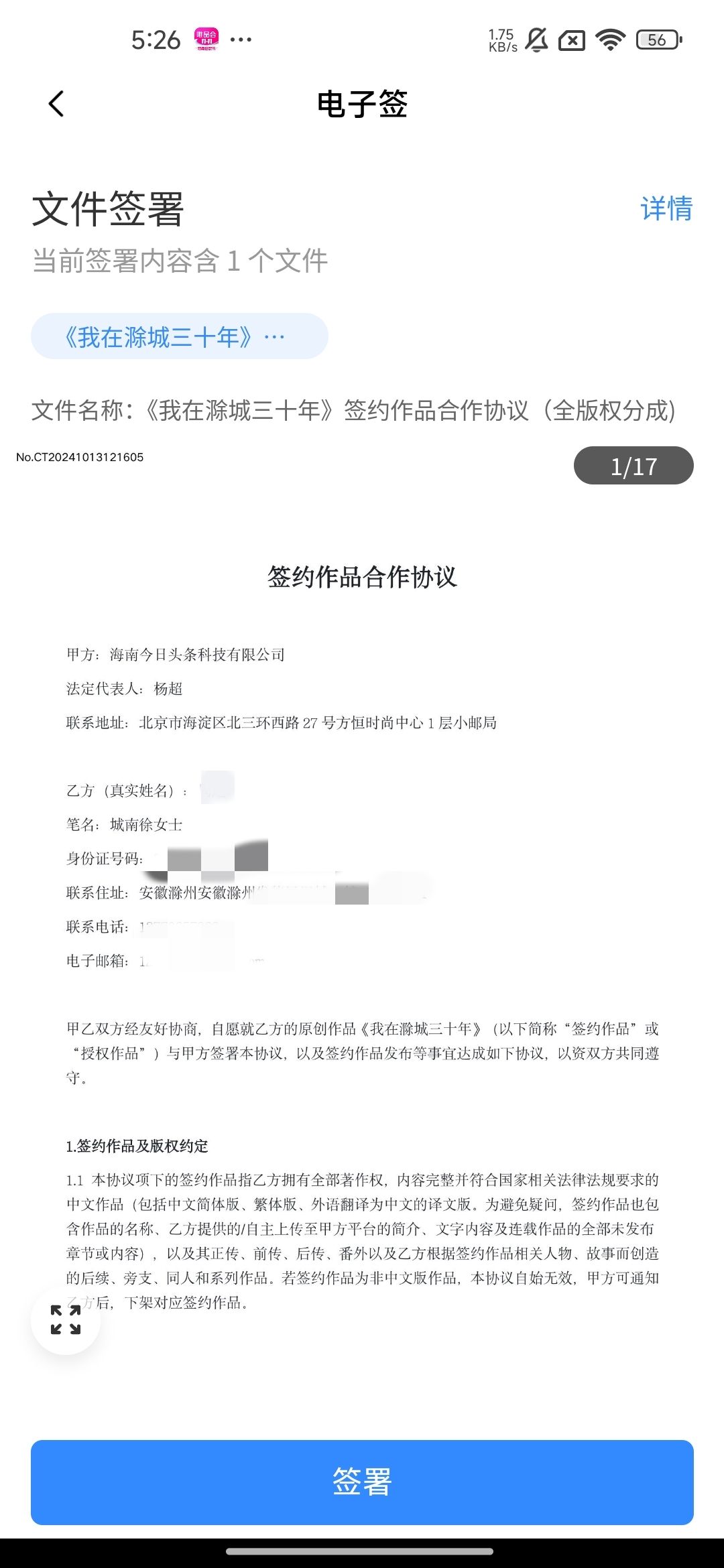
程晨的习惯性拒绝,很难接受很多外界事物,是因为她的性格有道裂缝。
五岁那年,她开始经常做梦;七岁那年,她的母亲在一个平常的早晨出了门之后,就再也没有回过家;八岁那年,程晨问父亲:“妈妈呢?”
父亲听到程晨问母亲的去向,恶狠狠地回道:“你妈死了!”
死了?
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,还不能够完全明白,失去母亲对于她今后的成长会有什么的影响。但她知道,死亡意味着失去,意味着她和别的同学不再一样,她比别的同学少了妈妈。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,同学们开始意识到,程晨的状态和从前不太一样,她再也不愿意张开嘴巴和别人交流,即便交流,也紧张地说不完整一句话。
同学们也开始察觉,再也没有见过程晨的妈妈。
程晨的妈妈谢川萍在和程晨的爸爸“结婚”之前,有过一段十年的婚姻,还有一个孩子。

1992年,经人介绍,谢川萍背井离乡,离开四川老家,到了滁城,认识了张维民。
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步骤繁多,事情繁琐,1992年,张维民从他的母亲那里要了个缝纫机,又找亲戚熟人打了一套新的衣橱和写字台,还没有来得及把赊账的家具钱还清,就和谢川萍把婚结了。
张维民还有一个弟弟叫张维军,比张维民小三四岁。张维民结了婚之后,次年生了儿子,给他取名阿飞,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阿飞能够从普通寻常百姓家出人头地,一飞冲天,过上好的日子。
随着人口增加,给本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一些生活的压力。一家不容三家姓,不分家门不安静。在母亲兰芝,也就是阿飞的奶奶要求之下,张维民和谢川萍带着一岁的阿飞从大家庭中分了出去,也就是分家了。
从前,为了避免家庭矛盾,减少家庭内部的争吵,在农村地区,结婚后大多数会进行分家,其实就是分开居住,经济独立,土地再分配。因为穷,很多家庭会因为钱而争吵,也就是穷吵。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,吵架的频率会渐渐减少。
因为兰芝还有一个小儿子,分家的时候并没有给张维民一些积蓄,只是在张维民再三的坚持下,把家里唯一的一台缝纫机要了过来。
从此,一家三口便开始准备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。有了三亩良田,两间小屋,一台缝纫机,原本只要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,生活也能够奔小康。
但老儿子大孙子,老太太的命根子。
从前,人们普遍早婚多育,很多女性在二十岁之前就结婚生子,一个女人可能会生下十多个孩子。由于从前的教育资源有限,人们的财富和经验往往是通过长期的生活积累起来的。
因此,年纪越大,财富和经验越丰富。老人们常以此说服年轻一代:“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,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,你懂什么?”
在大家庭中,老人对众多儿孙并非平等对待,他们往往更偏爱老儿子和大孙子。这种偏爱并非仅仅出于亲情,更是出于一种投资的心态,是为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所依靠。
以一个例子来说明,如果一个女性二十岁生子,那么她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大儿子。等到她年老,七十五年的时候,大儿子也已经五十五岁了。由于当时的生活条件,人们的寿命普遍较短,健康状况不佳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需要帮助,年迈的大儿子可能已经力不从心。
那么,我们再来看看老儿子。按照当时的生育习惯,女性在四十六岁之前都属于生育年龄。如果老儿子是女性四十五岁时所生,那么到她七十五岁时,老儿子只有三十岁,正值壮年,是老人最依赖的力量。再来看大孙子,当老人七十五岁时,大儿子五十五岁,大孙子则是三十五岁。
对于老人来说,大孙子也是重要的依靠。而小孙子则不同,当老人七十五岁时,小儿子才二三十岁,他的孩子最大的也只有十岁,显然是无法依靠的,年龄更小的孙子更是如此。
故而,兰芝心里跟明镜儿似的,清楚自己的命根子在何处。每次逢年过节,但凡有好东西、美味佳肴,她首先惦念的便是老儿子张维军和大孙子阿飞。平时吃饭,若有好菜好肉,她也定会把分家出去的大孙子阿飞唤来共享。
这样的场景持续了三四年。
从外地嫁到滁城的谢川萍心中总是充满了不满和怨恨。每当她看到张维民的弟弟享受着美酒佳肴,或是兰芝将珍贵物品送给张维军时,谢川萍的内心便会燃起熊熊怒火。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,而这种不公正是对她自尊心的一种无情践踏。
于是,她开始和兰芝争辩,希望兰芝一碗水能够端平。但谢川萍多次的挣扎反抗和据理抗争,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。争吵和唾骂等负面情绪并没有让她感到满足,反而使她的心情愈发沉重。
这种沉重的心情不仅积压在谢川萍身上,也积压在她的丈夫张维民内心深处。二十多年的日子,他比谢川萍更明白这种处境和心情。
九岁那年,张维民想吃锅里最后一小块锅巴,他走进厨房,一锅、一桌、一个破旧的碗厨,地上的猪食桶里还装着前几天煮好的红薯。张维民搬着个小板凳,小心翼翼地放在锅灶前,站上板凳,打开锅盖,他看见了锅里最后一块锅巴,那可是农村大铁锅煮饭后留下的精华!锅底的米饭在几把柴火的加持下变得金黄酥脆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对于很多孩子来说,这就是他们童年时最爱的美味之一。
这时,弟弟张维军跑了进来,跟哥哥说:“我还想吃锅巴。”张维民站在板凳上俯瞰着弟弟,他回答道:“还剩最后一块,我们俩一人一半,好不好?”弟弟:“不行,锅巴太小了,我要吃。”弟弟一边说,居然一边哭了起来。妈妈兰芝听到厨房里的哭声,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兰芝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,问了弟弟为什么哭,了解了一下情况,然后将锅里的锅巴拿出来递给了弟弟。
张维民气得跺脚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突然,他的泪水像喷泉一样,汹涌而出,一边哭一边抱怨母亲的举动。然而,兰芝并没有安慰他或解释为什么给弟弟。相反,她狠狠地扇了张维民一巴掌,打得他脸上火辣辣地疼。更糟糕的是,那颗每天都在摇晃、快要换的门牙,也在这一巴掌下彻底脱落。
从那一刻起,张维民对母亲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明白了母亲的爱是有差别的,有深有浅,有高有低。阿飞十岁那年,父亲患病。妻子川萍和母亲兰芝的一次又一次抗争,没有敲醒兰芝,反而一次又一次的击打着阿飞父亲的内心。
长时间的郁闷心情终于在一次川萍和兰芝的争吵中停滞。阿飞父亲被送进了医院。因为气滞血瘀,肝气郁结,身体被长时间的负面情绪积压,父亲得了病。
十岁的阿飞看着医生的脸,听见医生告诉母亲谢川萍:“肝癌晚期。”
从前的农村,谈癌色变,癌症等于死亡。在谢川萍和兰芝的又一次争吵中,阿飞的父亲去世了。
留给阿飞的没有什么遗产,只有十岁之前,每次跟着父亲去田间地头的记忆。
从前的早晨,父亲会带着阿飞去水稻田里回收前一天放进去的黄鳝笼子,把笼子全部回收,在屋子的门前进行整理倾倒。
每次倾倒时,都会围着许多周边的孩子,看着这些活蹦乱跳的黄鳝,孩子们不但没有一丝害怕,反而是手舞足蹈的高兴,大的,小的,小鱼,小虾,每一条笼子的打开,带来的都是快乐。
甚至有几次,倒出来的不是黄鳝,是蛇,孩子们反而惊奇和兴奋。
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力量,能够活着,活蹦乱跳的活着,总比死的好。
但阿飞的父亲确实是离他远去。
后来,阿飞的母亲也离他远去。

人的姓名是一个代号,有的人代号好听,有的人代号一般,就像吉祥数字一样,人们总是爱惜自己身上的所有羽毛。
阿飞的奶奶名叫兰芝,至于姓什么,徐思思不得而知,就像徐思思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外婆姓甚名啥。
姓名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只是一个代号,随着生命的逝去,这个代号便消失不在。
现在,阿飞的父亲消失了。
消失前的那些日子,阿飞至今回想起来,依旧历历在目。
2002年的10月2号清晨,天空中飘起了濛濛细雨,张维民像往常一样,穿上雨靴,披上雨披,带着一个破旧的草帽,挑着个空担子准备出门去收集前一天放出去的黄鳝笼子。
十岁的阿飞正是放国庆节假期,也想和父亲一同出去收黄鳝笼子。父亲抬头望着濛濛细雨的天空,低头对站在门口的阿飞说:“天空快要下大雨了,田间地头的路不好走,很滑,你就在家等我,我很快就回来了。”
阿飞站在门口对独自一个人出门的父亲说:“你一定要快点回来!”
十月的滁城,秋高气爽,早晨的雾气悬在一块块稻田中夹杂的池塘上空,金黄的稻谷叶上,露水还没有被刚出来的晨曦带走,空气中还有泥土散发的味道,夹杂着青草的香。
张维民挑着担子,收了几个笼子,前方的田埂上有一处人工挖出的,可能是为了放干稻田里剩余的水,准备收割稻谷的缺口。张维民一个跨步,脚跨了过去,但由于挑着担子,重心不稳,加上雨天草滑,张维民带着担子、笼子,重重的摔在稻田边上。
雨下的越来越大,雨水直直的砸在躺在土地上的张维民脸上,张维民手撑着地,试图爬起来,但肚子的一阵剧痛,让张维民又躺了回去。张维民一手握着挑担子的扁担,一手捂着肚子,他感觉这种痛和平常的猫抓狗咬的瞬间痛感不一样,此时的痛是像有人拿着针间歇式的扎在张维民的腹部,每次扎几分钟,停下来后,还没等张维民喘过来气,又继续接着扎。张维民躺在地上,疼痛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,含着血丝的眼球在眼眶中转来转去,泪腺分泌的体液夹杂着雨水。
雨下的越来越大。
不知过了多久,张维民听到有人呼喊:“维民,维民,你在哪?”虽然距离很远,但张维民一下就分辨出是认识了十年的妻子,谢川萍的声音。
跟在谢川萍的声音后,还有:“爸爸,爸爸,你在哪?”
阿飞孩子般纤细的声音划破长空。
在谢川萍的帮助下,张维民重新站立起来。阿飞说:“爸爸,我扶着你。”
(未完待续……)

